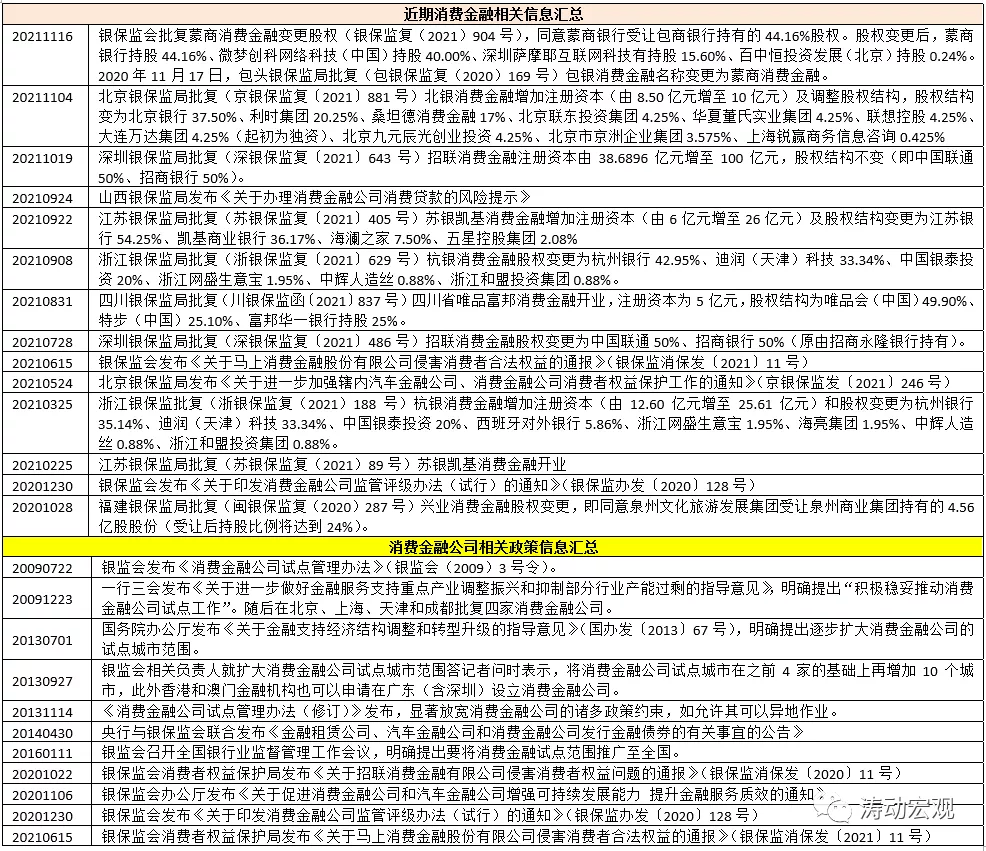牧户信贷特征及决策影响因素研究——以内蒙古纯牧户为例,下面是和融发展给大家的分享,一起来看看。
正蓝旗农行贷款
「摘要」了解牧户信贷市场特征和信贷行为及规模决策影响因素,对金融资本精准流向草原畜牧业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内蒙古纯牧户的田野调查数据,分析现阶段牧户信贷市场的基本特征,运用Heckman模型探讨牧户信贷行为及规模决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66.3%的样本牧户存在信贷行为,52.2%的牧户存在信贷约束,主要是“供给型”约束;牧户信贷规模具有“额度偏小、差异较大”的特点;95.7%的牧户发生正规信贷,7%的牧户发生非正规信贷,二者存在互补关系;“融资难、贷款贵”问题仍然存在;牧户信贷主要用于生产性支出,户均4.9万元,具有“发展型为主、生存型为辅”的结构特点;牧户信贷履约率高,但存在循环贷现象。牧户个人、家庭、生产、社会、市场、组织化等因素均会显著影响牧户信贷选择及规模。据此,提出创新信贷产品、探索牧户增信模式、注重金融知识宣教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牧户;信贷市场;信贷特征;信贷规模;影响因素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单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充分表明中央对金融业加大支持乡村振兴力度有更高期待。信贷资金作为可变要素的投入来源,能够优化农业生产初始禀赋投入(Ugoani,2013),促进农户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水平和生产经营能力提升(李长生、张文棋,2015),进而增进农户福利(Kumar et al.,2020);农区如此,占我国国土面积42%且拥有37亿亩草原的牧区亦然。然而,从需求侧来看,和农区相比较,牧区乡村振兴尤其是草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持续性的金融活水流入,但现阶段牧户生产生活中的信贷有何特点?需求规模有多大?哪些因素影响牧户信贷行为及其规模?牧户需要哪类金融产品和服务?如何创新牧区信贷供给方式?回答好上述问题对牧区金融市场化改革向纵深拓展、信贷资金更多更精准地滴灌草原畜牧业,进而带动牧户增收至关重要。
农牧户的信贷获得由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回顾以往文献,国内外学者有关信贷获得的研究主要以农户为对象,且集中在信贷约束、信贷可得性两个方面。关于信贷约束,普遍认为农户面临“需求型”和“供给型”两类约束(Boucher et al.,2008),且前者程度要大于后者(李成友等,2019)。哪类农户面临信贷约束及程度多大?主要是无土地产权农户(Piza & de Moura,2015)、土地规模(Swain,2007)或土地转入规模较大农户(路晓蒙、吴雨,2021)、社会资本较少农户(Reyes & Lensink,2011);中等收入农户面临的正规信贷约束较为严峻(彭克强等,2019),相对贫穷、富裕农户分别面临完全、部分“供给型”正规信贷约束(李岩等,2013);种粮大户的正规信贷约束程度高达78.89%(宁国强等,2016);同时,穷人因没有财力投资于社会资本导致其进入非正规信贷市场的概率较低(Yuan & Xu,2015)。
关于信贷可得性,学者主要关注其来源、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提高可得性。农户信贷主要源于存在互补关系的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胡金焱、张博,2014);尽管需求旺盛,但农户正规信贷可获得性较低,抵押和担保是主要方式,非正规部门仍是农户满足需求的主要渠道(刘西川等,2014)。已有关于信贷可得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何广文等,2018)、家庭(马燕妮、霍学喜,2017)、社会(邸玉玺、郑少锋,2022)、市场(汪昌云等,2014)等方面,近年来开始探讨普惠金融(樊文翔,2021)、数字技术(柳松等,2020)、金融素养(刘自强、樊俊颖,2019;乌云花等,2022)等对农户信贷可得性的作用。至于如何减少农户信贷约束,可行措施包括深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如农地确权或农地抵押(米运生等,2020)、加入产业链组织(周月书等,2019)、银保互联(彭澎等,2018)、发展合作金融(董晓林等,2016)和非正规金融(张兵、张宁,2012)等。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学者对农区农户信贷的研究比较丰富,而对牧区牧户信贷的关注略有不足,无论是在牧区信贷市场特征还是在牧户信贷可得性方面,基于微观调查的论证均较少,且多数是将农户和牧户相混合进行分析(隋艳颖、马晓河,2011;郭志仪、吴桢,2013),鲜有基于纯牧户的研究。谭文列婧等(2012)发现牧户普遍存在借贷需求但满足率较低,其借贷资金来源多样,正规渠道占比更高、规模更大,且多用于维持生产。马晶、朱美龄(2016)基于在新疆的调查,指出70.6%的牧户存在信贷需求但满足需求是以高昂成本为代价,约20%的牧户因缺乏必要的抵押和担保而导致需求得不到满足,低收入牧户存在金融排斥,且牧户的生产性贷款多于消费性贷款。事实上,牧区和农区存在天然区别,一方面,农业生产是“人-土地-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而牧业生产则增加关键要素“牲畜”;另一方面,农区的生产经营是在固定农地上的精耕细作,牧区的生产经营则易受外界因素影响,自然资源强异质性、草原荒漠化、气候多变性、灾害频繁性以及牧户脆弱性等使得牧区生产经营异常复杂。因此,上述有关农户信贷约束、信贷可得性的研究结果未必完全适用于牧区牧户。基于此,本文聚焦于牧区信贷市场尤其是纯牧户信贷需求,以内蒙古为例,利用8个纯牧业或半农半牧旗347户纯牧户的实地勘查数据,分析现阶段牧户信贷参与度、约束、规模、来源、用途、合约以及履约状况等市场基本特征,并运用Heckman模型识别影响牧户信贷行为及规模决策的因素,旨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时期牧区金融机构能够以牧户为主要客群且根据草原畜牧业生产经营特点精准创新和供给信贷产品及服务提供决策参考。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于2020年7~9月在内蒙古8个纯牧业或半农半牧旗的牧区进行的入户调查,具体包括新巴尔虎右旗(简称新右旗)、科尔沁右翼前旗(简称科右前旗)、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正蓝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简称达茂旗)、乌审旗、额济纳旗;在每个旗的牧区选择2个苏木(即乡镇),在每个苏木选择2个嘎查(即村),在每个嘎查入户调查10~15户牧户,共勘查360户纯牧户,获取有效问卷347份,有效率为96.39%;其中,新右旗41户、科右前旗50户、扎鲁特旗42户、阿鲁科尔沁旗47户、正蓝旗31户、达茂旗55户、乌审旗40户、额济纳旗41户。调查内容包括牧户家庭基本情况(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状况、户主养殖经验)、生产经营特征(草场面积、牲畜养殖数量、生产性资产、牲畜养殖收入)、收入支出概况、信贷、储蓄、保险、技术培训、社会化服务等信息。
受访牧户的基本特征见表1。户主绝大多数是男性,比例为91.6%。户主年龄主要集中在40~60岁,合计比例达到70.3%。户主受教育水平以初中、小学及以下居多,合计比例达到75.5%,说明牧户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牧户拥有的自然资本即草场的面积差异较大,其中50公顷以内的牧户占21.6%,300公顷以上的占33.1%,原因是8个调查地区分布在内蒙古东中西部,草场资源禀赋差异较大,总体呈现“东西部大、中部小,北部大、南部小”的特点,其中额济纳旗的户均草场面积最大,有5167公顷,但多是荒漠草原,生产力较低;其次是新右旗和科右前旗,户均草场分别为436公顷和349公顷,生产力较高;最后是正蓝旗,户均52公顷。因牧户草场资源的较大差异导致其牲畜存栏量也存在相似特点,受益于科尔沁草原和呼伦贝尔草原的优质生产条件,科右前旗和新右旗的户均牲畜存栏量较大,分别是1213个羊单位和592个羊单位;其次是额济纳旗,户均482个羊单位,以山羊和骆驼为主;最后是正蓝旗,户均212个羊单位。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本文使用牧户“是否参与信贷市场”与“信贷规模”,即金额作为被解释变量。
2.解释变量。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选取牧户户主个人特征(户主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特征(赡养比、2019年畜牧业收入占比、有无储蓄、参与养老或医疗保险、有无wifi或移动网络)、畜牧业生产特征(人均草场面积、2019年人均牲畜养殖规模、2019年人均年生产性资产价值)、社会特征(2019年礼金支出、距旗政府距离)、信贷市场特征(信贷利率、参与金融机构提供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化特征(参与技术培训、加入农牧业专业合作社)等6类16个变量作为影响牧户信贷规模的因素。另外,本文按照内蒙古地域将8个旗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作为实证模型的控制变量,且以西部地区作为对照组;其中,东部地区包括新右旗、科右前旗、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中部地区包括正蓝旗、达茂旗、乌审旗,西部地区包括额济纳旗。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2。
(三)模型设定(完整版详见知网)
三、结果与分析(一)内蒙古牧区信贷市场表征分析
1.牧户信贷参与度。在347户受访牧户中,66.3%的牧户有信贷行为(见表3),8个旗的牧户的信贷参与度均比较高,额济纳旗和新右旗牧户的信贷参与度最高,分别是78.1%和75.6%,达茂旗牧户的信贷参与度最低,为56.4%,说明现阶段内蒙古牧户普遍存在信贷行为,对信贷资金依赖较重;同时,牧户信贷需求远高于农户,何广文等(2018)在基于3省9县1730户农户的调查中发现,农户信贷参与度为40.75%,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牧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存在本质区别,现代畜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二是近年来消费者对牛羊肉的需求量持续增加和内蒙古牛羊市场价格稳中有升,促使多数牧户扩大养殖规模,进而对信贷资金的需求相应增加。
2.牧户信贷约束。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各家金融机构均在深耕牧区这片蓝海市场,本文将牧户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受信贷约束的牧户,指申请后获得全额贷款;另一类是受到信贷约束的牧户,指申请后被拒绝或未获得全额贷款。在347户受访牧户中,有52.2%的牧户存在信贷约束,主要是“供给型”约束,主要表现为牧户获批信贷额度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尤其是在新右旗和正蓝旗,分别有73.2%和67.7%的牧户面临信贷约束(见表3),科右前旗仅有34%的牧户存在信贷约束,由此可知,一是牧户仍面临“融资难”问题,牧区信贷约束仍较为普遍;二是牧户信贷约束程度高于农户,Li et al.(2013)发现61.5%的农户面临信贷约束,其中52%面临完全约束、9.5%面临部分约束,原因是畜牧业和种植业在生产经营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前者生产周期长、资金回收慢,且在生产周期内需要不断增加资金投入;三是各旗县牧户面临的信贷约束存在较大差异,这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
3.牧户信贷规模。有21.7%的牧户的信贷额度在5万元及以下(见表4),有26.1%的牧户的信贷额度在5万~10万元之间,各有17.8%的牧户的信贷额度在10万~15万元之间和20万元以上,另有16.6%的牧户的信贷额度在15万~20万元之间;同时,在230户有信贷行为的牧户中,户均信贷数量为15.4万元,最小值为1.2万元,最大值为62万元。因此,内蒙古牧户信贷规模具有“额度偏小、差异较大”的特点,说明牧户信贷规模存在异质性,一是体现在不同地域,草场资源禀赋好的新右旗和差的额济纳旗的牧户信贷规模较大,分别是21.3万元和20.6万元,其他六个地区牧户信贷规模均在10万~18万元;二是体现在不同牧户,原因是牧户信贷与其畜牧业生产经营规模密切相关,草场面积大、牲畜养殖多的牧户,其需要的生产投入比较高,故而信贷规模比较大。在有信贷行为的牧户中,草场面积在样本均值819公顷上、下的牧户的信贷规模户均分别为20.9万元、14.8万元,牲畜存栏量在样本均值197个羊单位上、下的牧户的信贷规模户均分别为18.7万元、14.2万元。
4.牧户信贷来源。牧户信贷市场的供给方由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构成,前者也称正规金融,包括农信社、商业银行(主要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蒙商银行等)、村镇银行和牧区资金互助社;后者也称非正规金融,包括亲朋好友、邻居和民间借贷者等。在有信贷行为的样本户中,有95.7%的牧户发生正规信贷,有7%的牧户发生非正规信贷,同时发生两类信贷的牧户仅有3.5%,说明内蒙古牧户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间的信贷存在互补关系,但正规信贷是牧户融资的主要渠道,若正规金融市场不能完全满足牧户的资金需求,则其可以选择非正规部门进行融资,这与杨汝岱等(2011)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说明近年来随着我国乡土社会逐渐向市民社会过渡,牧区以亲缘为基础的乡村社会关系在弱化,非正规信贷的规模和作用也在不断减弱,故在满足牧户融资需求方面,正规信贷因在贷款规模和风险控制上优于非正规信贷,已成为牧区金融市场发展的长期趋势。由表4可知,一是正规信贷额度较高;来自正规部门的信贷户均15.5万元,而非正规信贷户均7.9万元,说明在满足牧户大额融资需求方面,正规信贷要比非正规信贷更具优势。二是农信社和商业银行是牧户正规信贷的主要供给者;在220户发生正规信贷的牧户中,有90.9%的牧户从农信社获批贷款,户均11.9万元;有38.6%的牧户从中国农业银行获批贷款,户均12.1万元;有24.5%的牧户从其他金融机构获批贷款,户均10.1万元。牧户选择从农信社贷款的原因是多年以来农信社一直采用“整村推进、循环倒贷”运营模式,牧户已习惯于通过此方式维护贷款;牧户选择农业银行贷款是因有政府贴息。三是亲朋好友借款是牧户获得非正规信贷的主要渠道;在16户发生非正规信贷的牧户中,有81.3%的牧户选择从亲朋好友获得借款,户均8.1万元;仅有3户参与民间借贷,户均7万元,参与率较低既是因民间借贷利率较高且风险较大,也是因近年来内蒙古各地牧区纷纷加大对民间借贷的规范管理力度。
5.牧户信贷合约。内蒙古牧户的信贷合约因其来源有别而在期限、利率、抵押担保等方面具有差异性。由表5可知,一是牧户信贷合约多是短期,但来自正规部门信贷的期限普遍长于非正规部门。例如,农业银行贷款的平均期限为3年,农信社及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平均期限为2年,民间借贷的平均期限为1年,亲朋好友借款的平均期限为2年。牧户以短期为主的信贷合约,一方面是因为畜牧业生产具有季节性,信贷是为满足周转需求;另一方面是因为绝大多数正规信贷均有利息支出,牧户会慎重考虑贷款期限,且金融机构为降低信贷风险也会设置期限条件。二是正规信贷的成本较高。例如,农业银行、农信社及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平均利率分别为5.7%、8.2%和7.7%,民间借贷、亲朋好友借款的平均利率分别为13%和5.8%,也有部分贷款不计利息,说明内蒙古牧户的“贷款贵”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其中一个原因是牧区管理半径较大、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且牧户居住分散,相邻牧户距离可能在5~10公里及以上,金融机构物理网点的相对不足导致其在授信过程中的各类成本均较高,故未来可通过移动互联网金融降低交易成本。三是正规部门的贷款条件要求较高,主要体现在担保、抵押等方面。在220户有正规信贷行为的牧户中,有40%的牧户采用联保形式,多为三户或五户联保;有24.1%的牧户采取信用贷款形式;有22.7%的牧户采取担保形式;仅有7.3%的牧户通过抵押获批贷款;另有3.6%的牧户通过“政府+保险+银行”“担保公司+牧户”“龙头企业+合作社+牧户”等模式申请获批贷款,主要集中在大规模牧户或家庭牧场。在16户有非正规信贷的牧户中,贷款合约主要为联保、打借条或口头约定。虽然在实地访谈中牧户普遍反映现阶段只要符合授信条件,金融机构对额度较低、期限较短信贷的放款效率较高,原因是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普惠金融覆盖面的扩大和牧区金融供给市场的激烈竞争,但牧户若要申请获批额度较高、期限较长的贷款仍需有效的抵押品,而这恰是牧户短板,其牲畜棚圈、机械设备、草场经营权等动产或不动产的抵押在实践中仍面临可操作性差等难题;同时,上述发现也反映出牧区供应链金融、产业链金融市场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6.牧户信贷用途。在有信贷行为的牧户中,用于生产性、生活性支出的信贷资金户均分别为4.9万元、1.6万元,说明现阶段内蒙古牧户信贷的用途具有多元化特点,但主要用于生产性支出,且信贷需求具有“发展型为主、生存型为辅”的结构特点。在生产性信贷中(见表6),有31.9%牧户的贷款是用于购买牲畜,户均15.1万元,且主要集中在新右旗、科右前旗、扎鲁特旗等内蒙古东部地区,均是因近年来肉牛养殖市场利好,牧户通过信贷扩大再生产。有20.6%牧户的贷款用于购置生产设备,户均9.8万元,主要是近年来国家财政对牧户购置各类畜牧业生产机械提供补贴。有16.2%牧户的贷款用于购买饲草料,户均7.7万元,主要是近年来牧区气候干旱导致牧户饲草料面临季节性短缺,尤其是牲畜饲养的越冬问题。有14.2%牧户的贷款用于建造维修加固牲畜棚圈,户均6.7万元。有12.6%牧户的贷款用于租赁草场,户均6万元,主要是因近年来牧区草场“三权分置”改革后基于市场机制的草场流转较为普遍,在受访牧户中有高于1/4的牧户存在草场租入行为。有4.5%牧户的贷款用于建设及维护网围栏,户均2.1万元,原因是围栏的有效使用期限是5年,但经过不断维护可使用10年。
在生活性信贷中,有37.3%牧户的贷款用于购置或装修房屋,户均10.5万元,主要是因牧区新型城镇化和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进,多数牧户均在城里有房。有23%牧户的贷款用于购置车辆,户均6.5万元,在受访牧户中有303户家中有摩托车、有255户家中有轿车、有193户家中有拖拉机、有169户家中有三轮车、有72户家中有卡车。有17.3%牧户的贷款用于看病治病,户均4.9万元,原因是牧区也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受访牧户家庭中至少有1位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为29.1%,且留守牧区从事畜牧业生产的牧民的平均年龄也在45岁以上,同时受访牧户家庭中至少有1位成员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比例为8.4%。有9.7%牧户的贷款用于子女教育,户均2.7万元,在受访牧户家庭中至少有1位年龄在10岁以下人口的比例为41.2%。有9.1%牧户的贷款用于人情往来,户均2.6万元;在与牧户的深度访谈中,牧户普遍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人情消费不可避免,这无形中会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在牧户彼此间请与送的过程中,夹杂着攀比心理、补偿心理、从众心理等,请客的档次越来越高,礼金越来越厚。有3.6%牧户的贷款用于观光旅游,户均1万元,原因是随着牧户收入增加,以观光旅游为代表的休闲支出正逐渐成为其家庭消费支出的一个类别。
7.牧户履约状况。在有信贷行为的牧户中可按时履约的有94.4%,说明内蒙古牧户的信贷履约率高;不能按时偿还贷款的牧户主要是因收入偏低、资金用于应对突发事件以及信贷金额较高等。然而,进一步调查发现,部分牧户存在“以贷还贷、以贷养贷”的循环贷现象。在信贷合约到期时如果没有足够资金还款,有77户牧户会选择“借新还旧”,有60户牧户会选择“先还利息,本金续借”。另外,在实地调查中发现,金融机构对牧户存在多头授信、重复授信问题,受访牧户普遍在2~3家机构有信贷行为,由此可能引发过度授信进而成为一类重要的风险源。
(二)牧户信贷行为及规模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牧户在信贷决策中具有较强的自选择性,影响其是否选择信贷的不可观测因素同时也会对其信贷规模决策产生影响。在347户牧户中有117户未选择信贷,即存在33.72%的信贷规模为0的样本,若在第二阶段分析中剔除这部分样本,单纯运用OLS回归可能会导致处理结果有偏。因此,本文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牧户信贷行为及规模决策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其中,模型1、模型3未控制地区变量;模型2、模型4控制地区变量。信贷行为决策方程与信贷规模决策方程的F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两阶段模型均成立;同时,第二阶段OLS回归方程的逆米尔斯比率IMR在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牧户的信贷行为存在选择性偏误,表明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是合理的。
1.牧户个人特征。年龄分别在1%与10%的显著性水平对牧户信贷选择与信贷规模具有负向影响,说明年轻牧户较年长牧户更愿意选择信贷以满足自身生产生活需要,并且随着年龄增加,其信贷规模呈减少趋势,原因是牧户年龄越大,思想可能越为保守,对资金风险可能更加谨慎,故而较为排斥金融资本;以受访牧户的平均年龄50岁为界,有52.7%的牧户的年龄在50岁及以下,其信贷规模户均为11.5万元,比年龄在50岁以上牧户的户均信贷规模高2.8万元。牧户受教育水平与是否选择信贷、信贷规模呈正向相关,均在5%的水平显著,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牧户,更有可能选择并获得信贷,且其信贷规模较受教育水平低的牧户更大,说明牧户受教育水平越高,一方面有利于人力资本形成,不仅能认识到资本对畜牧业生产的重要性,而且其金融素养水平也相对越高,对信贷政策、程序、成本、风险等各类信息均会有较为深入的理解,故其越有可能产生对外融资行为;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牧户,生产经营能力也越强,更倾向于采用新型畜牧业生产技术或生产模式(如进行畜产品加工或从事牧家乐等),故而需要更多的运营资金。数据显示,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牧户的户均信贷规模比学历为小学及以下牧户多8.6万元。然而,鉴于现阶段牧户受教育水平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但其金融知识则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来普及,故要加大金融资本对草原畜牧业的支持力度,可考虑强化对牧户金融知识的宣教。
2.牧户家庭特征。赡养比对牧户是否选择信贷、信贷规模在5%、1%的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随着牧户赡养压力增大,其家庭负担随之上升,生产能力与精力相应减小,故为缓解生活生产压力,选择信贷的可能性和信贷规模会更大。根据调查,没有赡养压力的牧户,即赡养比为0的牧户,其信贷发生率为64.86%,较有赡养压力的牧户低4.45%;在发生信贷行为的牧户中,有赡养压力的牧户户均信贷规模为16万元,较无赡养压力的牧户高0.63万元。畜牧业收入占比在1%的水平上对是否选择信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5%的水平上对牧户信贷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畜牧业作为牧户主业,占比较小的牧户的其他收入来源较多,还款能力较强,更愿意且更容易获得信贷,而在获得信贷的牧户中,随着畜牧业收入占比的增大,其信贷规模也随之扩大。调查发现,畜牧业收入占比0.5以下的牧户的信贷参与率为75%,户均信贷规模7.13万元;畜牧业收入占比0.5以上牧户的信贷参与率为62%,户均信贷规模11.6万元,分别降低13%和增加4.47万元,与实证结果一致。有无储蓄在1%的水平对牧户是否选择信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参与养老或医疗保险在10%的水平对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二者对信贷规模均不具有显著作用,原因是储蓄较多的牧户对外部资金依赖较小,信贷需求较低;在受访牧户中有储蓄牧户的信贷参与率为52.1%,而无储蓄牧户的信贷参与率为69.9%,二者相差近18个百分点;保险可为牧户生产生活提供风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增信作用;在有信贷行为的牧户中,参与保险的牧户的信贷参与率为67.83%,比未参与保险的牧户高约19.4%。有wifi或移动互联网对牧户是否选择信贷在10%的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牧户的互联网使用对其信贷选择具有积极作用,使用wifi或移动互联网的概率每增加1%,信贷选择的概率将增加53.5%,表明互联网使用有利于牧户快速学习金融知识,了解金融产品,增加牧户的借贷积极性;调查发现接入wifi或移动互联网的牧户,其信贷发生率为63%,较未接入牧户高35%。
3.牧户畜牧业生产特征。人均草场面积对牧户是否选择信贷与信贷规模均具有正向作用,且分别在10%和1%的水平显著。草场作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要素,牧户的草场面积越大,越需要更多的资金购买仔畜、饲料、牧机以及雇佣劳动力或兽医,故其信贷行为发生的概率越大,对信贷规模需求也越高。根据调查,人均草场面积在100公顷以下的牧户信贷参与率为59.67%,户均信贷规模9.6万元,均低于草场面积在100公顷及以上的牧户,后者的信贷参与率与户均信贷规模分别为80.77%,11.63万元。人均养殖规模与人均生产性资产价值分别在5%与10%的水平对牧户信贷行为决策具有负向作用,说明人均养殖规模与人均生产性资产价值作为家庭财富的象征,规模越大意味着牧户生产经营能力越强,资金更为雄厚,对外部融资需求较小。人均生产性资产价值在1%的水平对信贷规模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牧户的生产性资产较多,代表牧户拥有较强的履约能力,越容易获得信贷资金,牧户因信贷价格、抵押担保条件及交易成本高等因素受到各类信贷约束的概率会越低,故而其信贷规模可能会越大;在有信贷行为的牧户中,按时履约牧户的生产性资产价值比未按时履约牧户高约14万元。
4.牧户社会特征。人际关系在中国农村牧区的信贷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礼金支出是考察牧户社会资本是否丰富的重要指标,但回归结果显示其对牧户是否选择信贷与信贷规模的影响均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牧区相对于农区居住更加分散,社会资本发挥的作用有限,导致其对二者的影响不显著。距旗政府距离在10%的水平对牧户信贷行为决策具有正向影响,在5%的水平显著负向影响信贷规模,说明居住地距离旗县政府越近,金融信息传递渠道越通畅,牧户越了解信贷信息,办理信贷更为便利,信息获取成本与信贷交易成本越低,进而增加信贷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但与居住在旗县附近的牧户相比,居住在偏远地区的牧户可能因缺乏非牧就业机会导致收入来源较少,其对外部资金需求量更大,因此会扩大其信贷规模。在样本牧户中,距旗政府距离100公里以内65%的牧户参与信贷,户均信贷规模9.78万元,与距旗政府距离超过100公里的牧户仅相差1.13%和1.2万元,差距较小。
5.信贷市场特征。信贷利率对牧户信贷行为以及信贷规模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参与金融机构社会化服务仅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牧户是否选择信贷具有正向影响,牧户接受的金融信息越多,越容易了解更多的金融知识,其金融素养随之提高,不仅影响其信贷偏好和渠道选择,而且引导其提高金融决策能力和信贷市场参与度。在调查中发现,参与金融机构提供社会化服务的牧户的信贷参与率为81.44%,比未参与牧户高29.77%。
6.牧户组织化特征。参与技术培训和加入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分别在10%与5%水平显著正向影响牧户信贷行为决策,但对信贷规模影响不显著。参加与畜牧业生产相关的技术培训有利于提升牧户生产水平和改善其经营绩效,进而增强其信贷履约能力,提高牧户的信贷参与度;牧户加入农牧业专业合作社意味着牧户融入畜牧业产业链组织,一方面是合作社可为牧户提供生产技术指导与服务,提供稳定的销售渠道与市场,由此降低牧户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预期,使其有效信贷意愿增加;另一方面是合作社可作为牧户融资环节的中介桥梁,为牧户申请信贷提供增信支持,减少牧户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并对牧户获批信贷后的用途和履约形成有效制约,由此缓解高交易成本对牧户申请获批规模信贷的负向作用。参与技术培训和农牧业专业合作社的牧户信贷参与率为71.32%与70.64%,较未参与牧户分别高8.48%和6.77%。
(一)结论
深化牧区金融市场改革及为草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需要精准把握现阶段牧区金融市场的基本特点和影响牧户信贷可得性尤其是信贷规模的因素。研究表明,内蒙古牧户信贷参与程度较高,有66.3%的牧户存在信贷行为,但普遍面临“供给型”信贷约束,占比为52.2%,主要表现为获批信贷额度不能满足需求,说明牧户仍面临“融资难”问题;牧户信贷规模在不同地域、牧户间具有“额度偏小、差异较大”的特点;牧户信贷以来自正规部门为主,非正规部门为辅,两个部门信贷存在互补关系;牧户的“贷款贵”问题仍然存在,正规信贷合约虽然比非正规信贷的额度大、期限长,但其成本高、条件严;牧户信贷用途具有多元化特点,以生产性支出为主,户均4.9万元,超过生活性信贷支出3.3万元,说明现阶段内蒙古牧户信贷需求具有“发展型为主、生存型为辅”的结构特点;牧户信贷履约率高,但存在“以贷还贷、以贷养贷”的循环贷现象,且金融机构对牧户存在多头授信、重复授信问题。
牧户的个人、家庭、畜牧业生产、社会、信贷市场及其组织化特征等因素均会显著影响其信贷规模。在信贷行为决策方面,户主年龄、畜牧业收入占比、有无储蓄、人均养殖规模、人均生产性资产价值具有负向作用,户主受教育水平、赡养比、参与养老或医疗保险、人均草场面积、距旗政府距离、参与金融机构提供的社会化服务、有无wifi或移动网络、参与技术培训和加入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对牧户是否选择信贷具有正向作用;在信贷规模决策方面,户主年龄、距旗政府距离具有负向效应,户主受教育水平、赡养比、畜牧业收入占比、人均草场面积、人均生产性资产价值具有正向效应,均可激励其扩大信贷规模。
(二)政策启示
1.创新信贷产品,拓延牧户抵质押物。一方面,金融机构要根据牧户个人特征(如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家庭财富、生产经营水平、社会关系网络、过往信贷行为尤其是履约状况等因素有别产生的差异化资金需求,量体开发信贷产品,确保牧户的贷款规模与生产经营需求相匹配、贷款时点与资金需求时序相匹配、贷款期限与其畜牧业生产周期相匹配,以此提高牧户有效信贷的可得性。另一方面,探索试点牧区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各类不动产权证抵押贷款,对牧区从事畜产品生产加工的牧户尝试允许其利用养殖圈舍、厂房等类型的不动产进行抵押贷款;同时,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推进动产抵质押贷款,如牧业机具担保贷款,活体牲畜、存货、应收账款、存单、订单、保单等质押贷款。
2.探索牧户增信模式,发展产业链金融。在传统的牧户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实现增信的基础上,推广通过政策性扶持、担保、保险等市场工具为牧户申贷增信,如政银担、政银保等模式;同时,因牧户加入合作社有利于其扩大信贷规模,故要探索畜牧业全产业链融资模式,支持合作社、龙头企业为产业链上游的牧户提供担保等增信服务。
3.注重金融知识宣教,发展牧区数字金融。按照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加强农村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的要求,探索建立牧区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站,选派金融助理,长期进村入户,宣讲金融知识,提升牧户金融素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数字金融与信贷需求相融合,以手机银行APP、微信小程序或公众号为载体,推进牧区数字信贷建设,提高牧户办贷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牧户融资服务的便利性和满意度。
原文载于《农村金融研究》2023年第5期
乌审旗贷款
天天正能量:最能让人感到快乐的事,莫过于经过一番努力后,所有东西正慢慢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关于开展大中专毕业生实名登记的通知
为准确掌握乌审旗籍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针对性开展就业帮扶服务,制定和完善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相关政策,现继续开展大中专毕业生实名制登记工作,具体事宜如下:
一、实名登记对象
㈠2010年(含)—2016年(含)期间毕业的乌审旗籍未就业(意在乌审旗就业创业的)大中专毕业生,2014、2015年已登记过的人员不需要再重复登记。
㈡ 在乌审旗服务的各级各类储备人员和其他已实现稳定就业人员均不登记。
二、登记时间
从2016年5月6日起进行登记,如登记过程中有其他问题咨询,请及时与人社局联系,联系电话:0477-7582201。
三、登记地址
乌审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门户网(http://www.wsqrsj.gov.cn/),进入网页右下角“大学生实名登记系统”,按照自身实际情况进行登记。
四、服务事项
㈠通过电话、短信平台、网络等方式为已登记的毕业生提供各类招聘信息,及时将已登记的毕业生向企业进行推荐。
㈡对有创业意愿的已登记高校毕业生,经审核通过后,为其提供创业培训、政策咨询、创业指导、小额担保贷款、入驻大学生创业园等服务。
乌审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5月6日
-第623期-
栏目:通知公告
本期编辑:乌兰
新闻·通知·公告·文化·旅游·文明·生活
乌审旗发布 乌审新媒体的引领者
温馨提示:注:内容来源均采集于互联网,不要轻信任何,后果自负,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若本站收录的信息无意侵犯了贵司版权,请给我们来信(j7hr0a@163.com),我们会及时处理和回复。
原文地址"正蓝旗农行贷款(乌审旗贷款)":http://www.guoyinggangguan.com/dkzs/94404.html。

微信扫描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