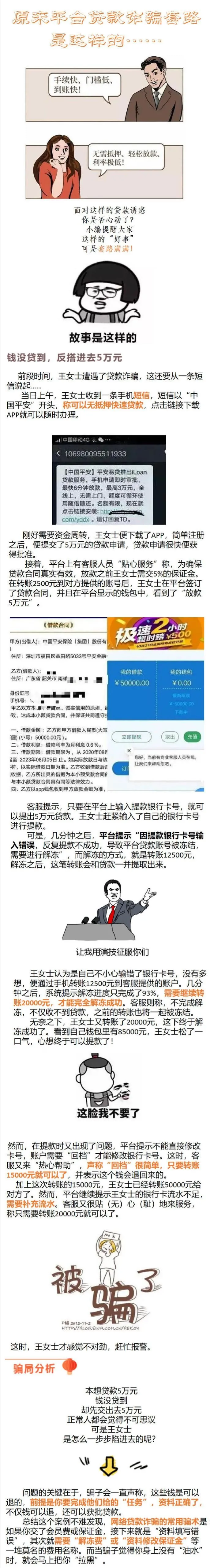转自“ cnuzgs”微信公众号。
·
·
·
摘要:宋代财政与经济的货币化进程中,王安石变法时期是一个关键时段。在宋神宗朝以前,北宋传统国家财政中的货币征收和使用权重相对有限。在两税、和买、专卖等领域中,货币主要作为征收物、支付手段、准价工具以及中转角色而存在。在实物主导的经济模式下,货币机制未能得到充分拓展。王安石变法开启了新的经济与财政模式,并以货币运作为导向。常平新法通行青苗钱借贷。在还贷时,虽然设置货币与实物双选可能性,但政府通过粮食基准价的设定,驱动农民选择货币还贷,实质上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货币借贷闭环,同时也引发了新旧两派关于实物与货币借贷的论战。免役法进一步拓展了货币化的广度与纵深,开始深入到基层劳役领域:劳役执行模式(雇募)、结算法(货币)、财政统筹(国家财政)三方面体现出免役法的深层变革逻辑,也是劳役货币化的基本逻辑。
关键词:青苗借贷;免役法;货币化;王安石变法
宋代货币的相关研究面向颇多,既有《两宋货币史》这样的通论,也有关于城乡货币经济、铜铁钱、纸币钞法、货币政策与流通等专题讨论。总体而言,北宋时期国家财政的货币化进程,尤其是王安石变法以来所形成的国家经济行为与财政中的货币化问题,因涉及大量新法细节,很少有人做过细致深入的研究。王安石变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上货币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变”事件。新法派对货币的理解(“泉布”“泉府”“轻重”“利孔”“开阖敛散”等)以及在新法系统中的尝试与广泛应用,产生于思想观念与创造力极为活跃但又积弊重重的北宋中后期,既有偶然性又有其必然性,它的成败与利弊纠葛长期以来深入人心。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课题。
一、北宋传统国家财政中的
货币征收和使用权重
在研究新法之前,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北宋传统国家财政中的货币征收和使用权重问题。宋代的常赋以实物为主,“岁赋之物,其类有四:曰谷,曰帛,曰金、铁,曰物产是也”。而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铜铁钱实际上只是“曰金、铁”之一类,占比非常少。以熙宁十年为例,当年夏税1696万贯石匹两,钱385万贯,占比22.7%;秋税3504万贯石匹两,钱173万贯,占比仅4.9%。货币(铜铁钱)在两税全年的占比也不过10.7%,十分有限。
上供物中经常存在折变现象,“一时所须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不管最终折成何种实物抑或是铜铁钱,折变行为并不影响两税征取的整体结构。此外,只要存在钱与实物的折算问题,很容易出现“倍折”与“贵折”现象:“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艰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在税赋系统中,钱既是征收对象之一,也是不同物产之间的“准价”工具。
两税中有折变,还有支移,“其输有常处,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两者存在一些有限的“货币化”空间。如“折斛钱”,将粮食折变为现钱征收;又有“脚钱”,“不愿支移而愿输道里脚价者”,即通过输钱来免除远途支移,“脚费,斗为钱五十六”。不管是因支移而增取的“地里脚钱”、部分州县“折斛钱”,还是少数地区的“丁身钱”,在赋税系统中仍占少数,不足以影响整体货币权重。
正赋之外,尚有和买、和籴,两者皆以货币为重要支付手段。所谓和买绢,即官方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向民间采购绢帛,“官给其直,或以钱,或以盐”。和买原则上倡导政府与百姓之间平价交易,但实际上很容易造成变相征取。到了南宋又衍生出“折帛钱”,其中和买绢部分折算成钱无偿收取,实质上演变成新税种。
和买与市籴应该是政府最大规模的以货币为主导的面向民间的集中采购了。比如元丰五年和买绢帛量“凡八百十六万一千七百八十匹两,三百四十六万二千缗有奇”,市籴规模往往会更大,神宗朝河东一地,其和籴规模要远超二税:“河东十三州二税,以石计凡三十九万二千有余,而和籴数八十二万四千有余。”缘边军储多仰赖于和买和籴,货币在国家财政中的支出量虽然大,但本质上也只是政府与基层交易中的支付工具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和买、和籴中的“预买钱”“预付钱”(对农民而言是“预借钱”),在形式上有点接近政府贷款。其主要形式是钱物或物物交易,朝廷出钱或盐,“旧以钱、盐三七分预给”,百姓输绢帛或粮食,特殊情况下还会再折算回钱。熙宁初,王广渊为京东转运使负责和买绢,“率千钱课绢一匹,其后和买并税绢,匹皆输钱千五百”。即转运司前一年出1000贯“预买”来年绢一匹,到了第二年和买绢连带正税绢每匹输钱1500贯。在这组操作名义上是“和买绢”,但钱折绢、绢又折成钱。政府预借给农民钱,第二年连本带利收回的还是钱。这在当时观感非常不好,“假和买绢之名,配以钱而取其五分之息”,程颢等认为王广渊是假借和买之名在放政府高利贷。这种行为其实并不罕见,由于年景、需求、奸猾操控等因素,政府采购的确存在不对等交易可能性。“初,预买绢务优直以利民,然犹未免烦民,后或令民折输钱,或物重而价轻,民力浸困,其终也,官不给直,而赋取益甚矣。”从形式上看,和买、和籴仍主导实物交易,钱在里面主要扮演支付和准价工具。然而钱、物反复相折,所有的溢价因素都会体现在价格上,致使“物重而价轻”,最终折算成钱而由百姓承担。
和买、和籴法中的政府预借或预付模式与后来的青苗、市易借贷,存在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这种实物为主导的借贷法在未来很有可能进一步走向货币化。仁宗朝以来的“陕西青苗钱”到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常平青苗钱”的转变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或者说,从偏实物型的政府预买预借法到偏货币型的青苗市易借贷法,这种政府“借贷”模式的演进是考察新法货币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视角,后文详述。
再考察一下朝廷的专卖财政。专卖法因时因地而变,往往万变不离其宗,此处以盐茶法为例。盐法一般有两种:或通商,向商人征收商税;或官卖,政府以盐本钱收盐,然后设场专卖。茶专卖要更严格一些,“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不得出境”“(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和盐法一样,以茶本钱收茶,“择要会之地”设场专卖,有点像政府统购统销模式。
与和买、预买法那种政府向基层百姓的单方面收购不同,茶、盐专卖还涉及更复杂的商贾交易或远程军事贸易。商贾贸易是专卖体系中至为重要的一环:商人通过缘边入中粮食而获得交引,于各地请盐之后再自行销售,或“至京师给以缗钱”。此外还有商人在京入纳金银钱帛而得盐、茶钞等。范祥改革盐政,推行钞盐法,商人向政府入纳实钱得盐钞,然后请盐销售。茶法类此,“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场茶”。
在这个体系中,作为专卖物资的茶、盐、香药等(在各地榷货务),作为军储的粟米粮食和马匹(入中或交易于缘边),和钱(入钱于京师或缘边),三者间形成一种特殊的三角贸易关系。军储仰赖商人入中,缘边需要粮、钱与马匹;京师开封府是茶盐等券钞贸易的集散地,对实钱的需求量非常大,“三四年间,有司以京师切须钱”“论者谓边籴偿以见钱,恐京师府藏不足以继”云云。于是,茶、盐、钱等成为了驱动商人进行远程投运和缘边军事贸易(如以茶博马等)的重要战略物资,后来还添入“东南缗钱、香药、犀齿”所谓“三说”等。
所有上述物资中,钱承担着多样灵活的“中间”角色。对商人而言,它既是支付、兑付手段,可以通过入纳钱来兑换茶、盐、香药等;同时也可以作为商人需求对象,比如这里说到的“东南缗钱”以及“入粟请钱”的“现钱法”等,致使京师的缗钱尤其紧俏。
纵观北宋传统国家财政中的货币运作,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其一,作为实际征取或变相征取的税收对象(比如两税、商税或折税钱等);其二,支移折变中,作为物与物之间的“准价”手段,以钱为媒介,折而又折;其三,作为大宗商品和专卖物资的重要支付手段(和买钱、籴本钱、茶本钱、盐本钱等);其四,在商贾介入的专卖贸易中则是关键性的兑付、中转物资。总之,北宋传统国家财政中货币运作已经多样化,政府也懂得如何通过货币(含券钞)进行各种细分运作,来达成所需要的实物变转和远程军事物资贸易。不过在这些经济行为中,实物性仍是其重要特征,货币机制依然主要服务于自然经济与实物经济模式。确切地说,货币机制与货币化进程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二、青苗法与青苗钱
那么,王安石变法到底带来了那些新的货币化尝试?它的货币运作的广度与深度又如何?抑或形成了哪些新的货币运作机制?
在国家经济和财政行为中(包括赋税、和买籴、征商、专榷、铸造、财政总体收支等),关于货币化考察有两个比较直观的面向:一个是货币在这些经济行为中的使用权重或占比问题,另一个则是货币机制的展开及其运作方式的多样化问题。王安石变法开启了新的经济与财政模式,我们自然也要对其中的货币化问题予以一番新的考察。因新法所涉及的货币面向太广,本文我们将以青苗、免役二法为中心进行考察。
熙宁二年九月,朝廷颁布青苗法。此次青苗法与旧常平法挂钩,常平仓原有敛散功能不变,在此基础上增加并突出借贷功能,所谓“新法之中,兼存旧法”:其一,通有无,广蓄积,欠时赈粜,平抑物价,灾伤赈济等,继续体现作为常平旧法职能,仍以实物赈贷为主。其二,提供青苗钱借贷,振小农乏绝,抑制兼并,此为新法职能。新法之“新”并非只是体现在政府借贷行为上,更重要在于其中的货币化导向。确切地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尝试以货币为主体的全国范围的政府借贷。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来看放贷(预支)环节。青苗放贷以货币为主体,“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预给”“其两仓见钱,依陕西出俵青苗钱例,每于夏秋未熟以前,约逐处收成时酌中物价,立定预支”。发放青苗钱是青苗借贷的通行法则,即使农民名义上申请粮食,政府仍以货币形式发放,如熙宁三年诏申明“其愿请斛斗者,即以时价估作钱数支给”。
常平新法以原常平、广惠仓为基盘,其物资储备以钱、粮食为主。“今诸路常平、广惠仓略计千五百万以上贯石”,又汇聚各路钱物,诸如“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买陕西盐钞钱”等。不过,待到发放青苗钱时,粮食也可以通过转运司进行钱斛兑换,转化为现钱放贷,“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其可以计会转运司用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预给”。总之,从各种执行条例上来看,政府给出去的主要是钱,即我们熟知的青苗钱。这一点与之前陕西青苗钱法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后续诏令往往会说明“陕西青苗钱例/法”,两者从放贷模式上来看非常接近。
再看青苗借贷规模。从熙宁到元丰年间,随着借贷本金的不断投入和青苗利息盈收等,到元丰后期,常平借贷规模已基本稳定在每年千万贯以上:元丰三年,散1318万贯石匹两,敛1500万;元丰四年,散1383万,敛1197万。其中元丰三年最高触及1500万贯石匹两,几乎可以匹敌熙宁十年的夏税规模。熙宁后期,常平总物资达3739.4万贯石匹两,而政府严格限定常平仓储投放比例“常留一半外,方得给散”,因此,这里所呈现的敛散量最多不过常平总体量的一半而已。
其次来看还贷环节,这是青苗借贷货币化导向的关键,也是新旧两派的核心争议所在。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建言:
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预给,令随税纳斛斗。内有愿给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
政府以现钱发给农民,后令其“随税纳斛斗”,这是通行给纳法。但为了保证百姓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官方设定在请贷时也可选择粮食(“内有愿给本色”),而还贷时也可以选择还钱(“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于是在“请钱纳斛”的基本模式下,原则上还可以有“请钱纳钱”“请斛纳钱”和“请斛纳斛”三种模式。不过这种货币与实物交错的借贷法在实际执行上是困难重重的:首先,给(贷)、纳(还)两端——给钱还是给粮、还钱还是还粮——缺乏统一标准;其次,除了“请钱纳钱”这种纯粹意义上的货币贷款之外,其他三种几乎都要涉及粮食价格在不同时期的反复折算。于是条例司又作补充:
其给常平、广惠仓钱,依陕西青苗钱法,于夏秋未熟已前,约逐处收成时酌中物价,立定预支每斗价,召民愿请。仍常以半为夏料,半为秋料。
所谓“酌中物价”,即权衡一段时间内粮价波动而确立的中间价格,相当于时价,作为当年的粮食基准价格。不过朝廷没有直接依从条例司的建议,而是重新规定了基准价格:
诏:常平、广惠仓等见钱,依陕西出俵青苗钱例,取当年以前十年内逐色斛斗一年丰熟时最低实直价例,立定预支,召人户情愿请领。……其愿请斛斗者,即以时价估作钱数支给,即不得亏损官本,却依见钱例纽斛斗送纳。
这则诏令信息量丰富,我们需要注意两点:第一,无论是名义上“借钱”还是“借粮”,政府实际给出的都是钱。“其愿请斛斗者,即以时价估作钱数支给”,即农民想要粮食,政府还是按“时估价”换算成钱发放给农民,令其自行买粮即可。第二,也就是说在出俵(放贷)时,无论最终采取哪种偿还模式,都要确立一个粮食基准价,为方便来年偿还时核算。于是,这个“粮食基准价”的设定就成了最关键要素。条例司最初给的建议是“约逐处收成时酌中物价”(即“时价”),但此条诏令则最终规定为“取当年以前十年内逐色斛斗一年丰熟时最低实直价例”,相当于以“十年最低价”为粮食基准价。为方便读者理解,笔者曾将这一诏令所内含的各种“政策信息”以数据模式,制成了一张常平青苗俵散及还纳本息示意表。我们假设还纳和请领“时价”为20文/斗,“十年内最低价”为10文/斗,官方向农户俵散1000文,见表1。
表1 常平青苗俵散及还纳本息示意表
经数据一换算我们可以发现,“请钱还钱”(请1000文还1200文)毫无疑问是最省心省钱模式,尤其是对农民而言。然而只要是“还斛斗”,给纳时就必须按照十年最低的价格进行换算,即借1000文,当还1200文,如果折算成粮食则需还120斗(按最低价10文/斗)。但因时价是20文/斗,这120斗就相当于2400文实值,这对农民来说既不划算也不现实。
这里笔者在“十年最低价”与“时价”之间只用了一倍价格差,但实际上也有可能不止一倍。可以说,政府相当于通过价格杠杆设置了一个还实物预亏的结果,以此驱使百姓主动选择以现钱还贷。当然,在现实中也不排除还贷的时候粮食时价与十年最低价相比高出不太多的情形,因为市场转易存在损耗与钱贵物轻等情况,农民宁可选择看上去不太划算的实物还贷。但绝大部分情况下,时价可能远远高出十年最低价,从而使农民在青苗借贷还纳时不可避免地趋向唯一一种官方认可的模式——请钱还钱。青苗借贷政策中以价格驱使农民纳钱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政府通过最低基准价的设定来引导农民选择还贷模式,而基准价与时价之间的差价越高,以现钱还贷为趋向的价格驱迫性因素就会越明显。而当时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对话更是明确指向这一点。
上曰:“俵青苗钱而纳米方贵,如何令纳?”安石曰:“贵则民自纳钱。”
上曰:“纳钱则仓但有钱,凶年何以振贷?”安石曰:“常平米既出尽,则常平但有钱。非但今法如此,虽旧法亦不免如此。”
王安石的表述非常直白,“贵则民自纳钱”的背后隐藏的正是以粮食基准价(价格政策)驱动货币还贷的基本逻辑。
总之,青苗法不管是借贷还是还贷方式,整体上都在推动或导向货币借贷。虽然依旧杂糅实物形式,比如在常平敛散“以钱银谷帛贯、石、匹、两定年额”,这本身也与常平仓性质,或者说常平新法兼通“实物赈贷”与“青苗借贷”两种属性相关。但总体而言,并不改变新法在常平借贷问题上的趋货币化尝试。这种趋向自然也被反对阵营看在眼里,成为青苗法争议的焦点。
熙宁三年,新旧两大阵营领袖——王安石与韩琦之间最重要的一次交锋,就是关于青苗借贷及其背后“国服之息”的辩论。两人穷尽经学理论,本质上无非“货币”与“实物”两套经济逻辑在对抗。反对者针对的其实并不是国家借贷行为本身,而是背后的货币化的取向。更确切地说,其质疑并不针对贷款发放的货币化,而是还纳本息的货币化。在他们眼里,常平旧法已经受到了新法功能的严重挤压,传统的实物型经济模式正在被新法主导的货币模式所“蚕食”。韩琦云:“去岁河朔丰熟,……若乘时收敛,遇贵出粜,不惟合于古制,而无失陷之弊,兼民实被惠,亦足收其羡赢。今诸仓方有籴入,而提举司亟令住止,盖尽要散充青苗钱,指望三分之利,收为己功。”
反对阵营主要有两个质疑点:首先是常平储备的货币化,即常平仓因货币储量的增加而影响到旧式常平赈贷法。如司马光言:“今闻条例司尽以常平仓钱为青苗钱,又以其谷换转运司钱。是欲尽坏常平,专行青苗也。”其次是常平借贷的货币化及其货币利息形式。这一点在论辩中明确地体现为两种“国服”理论——物息与钱息、实物敛散与货币敛散——之间的对抗。文彦博云:“此法(青苗法)于乡村之民行之,以待夏秋成熟,折还斛斗丝帛,即谓之举放;若只令纳本利见钱,即谓之课钱。”而对“课钱”担忧事实上正是新法实际执行中的“货币化”导向。
可以说,当时关于青苗法的几乎所有争议,诸如青苗息钱、钱荒问题以及“天子开课场”“有损国体”等,本质上都是来自于对新法所执行的货币化(“钱”)导向的忧虑。王安石变法通过政府借贷模式(青苗、市易借贷),以更直接、更彻底的方式将这个问题抛了出来并执行开来,首先要面对的便是来自传统儒家经济观念的挑战。韩琦、司马光等人的立场代表着传统自然经济与小农经济模式下,从生产本位出发的实物(物产)模式:“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此非民耕凿可得也,无兴贩以求之,是为教民弃本逐末耳。”“督民见钱与金银,求国富庶,所谓拥篲救火,挠水求清,欲火灭水清可得乎?”“两税不征粟帛而征钱,吏得为奸以病民。”在他们眼里农民手里只有物产,没有太多的钱,像青苗法这样的货币借贷体量是不可思议的,更何况已经“侵蚀”到旧常平的实物赈贷模式。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类似和买、和籴、陕西青苗这样的实物主导下的预买预借法,却不能容忍青苗借贷的根本原因。
三、免役法与免役钱
如果说青苗法与青苗钱代表着货币化性质与运作面向(货币借贷与货币利息),那么免役法则开启了货币化的广度与纵深,开始由赋税、征纳、仓储领域深入到劳役领域。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全国范围内的劳役“货币化”尝试。历史上租税征纳由从实物走向货币形态是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同样,劳役也经历了艰难的货币化尝试:由“差役”走向部分“雇役”,再到熙宁免役法的全体出钱“免役”。虽然最后还是被人为终止了,但免役法依然称得上是该进程中的一次激进变革,预示着未来劳役发展的方向与可能性。这一进程还需要从宋仁宗朝的衙前改革说起。
仁宗朝改革派立志整顿差役之弊,相继出台限田及乡户衙前等方案,然而收效甚微。之后,几乎所有人都将目光转向了雇募之法。英宗时,司马光提出:“凡农民租税之外,宜无所预,衙前当募人为之,以优重相补。”马端临评述云:“所谓募人充衙前,即熙宁之法也”,并言“(韩、蔡诸公)过欲验乡之阔狭、役之疏密而均之……衙前之弊如故也”“此王荆公雇募之法所以不容不行之熙丰欤!”在他看来,熙宁役法改革之变“差”为“募”是唯一出路。王夫之以为“免役之愈于差役也,当温公之时,朝士已群争之,不但安石之党也。民宁受免役之苛索,而终不愿差役者,率天下通古今而无异情”。后人对役法的走向其实已经形成一定共识。司马光在元祐时主张全面恢复“差役”而不留任何余地,其实并非一开始就反对雇募模式,而实为新法所激。
熙宁四年十一月,朝廷颁募役法:
诸户等第输钱,免其身役,官以所输钱,立直募人充役。输钱轻重,各随州县大小、户口贫富、土俗所宜。(小注:谓以家业钱或田亩或税钱之类。)计一岁募直及应用之数,留准备钱,不得过一分,立为岁额。仍随逐处均敷至第三或第四等,不足,听敷至第五等(小注:坊郭自随逐处等第均定。)即贫乏而无可输者勿敷。
从颁行条例来看,熙宁役法有几个核心特点:第一,全民输钱免役(少数户等除外),“诸户等第输钱”;第二,收拢的免役钱由政府统筹募役及支出;第三,输钱多少,因地制宜,“各随州县大小、户口贫富、土俗所宜”,并执行财产标准,“谓以家业钱或田亩或税钱之类”;第四,预留一分作为“准备金”以应对灾伤;第五,立定岁额,均敷到诸等户。在熙宁后期保甲执役政策出台之前,本次役改带来的最重要变化是:过去的乡村差役基本被免役输钱所取代(军员、官员代役除外),与此同时,相关役钱由国家支配、统一支出。
同样是募役需求,新役法与之前司马光等人倡导的“半募役”模式有着质的区别。第一,司马光、韩维等只是停留在“募役”部分替代“差役”这一步,并不排斥差役,但免役法却是排斥“差役”的,募役是唯一方案。第二,全民“免役”,民户一概缴纳免役钱或助役钱,以货币方式结算,实现基层统一货币化役改方案。第三,免役法还不光是简单货币化问题。汉武帝时“更赋”允许个体之间私自货币结算,不经由国家,但熙丰免役钱的收支结算则要求统一经由政府之手,由政府来主导完成财政统筹、转移支出。这与个体“私自雇役”还是国家层面的“局部雇役”,都有本质区别。而这三层在役法改革诉求方面是逐步递进的,分别从劳役执行模式(雇募)、结算法(货币)、财政统筹(国家财政)三个方面体现出免役法的深层变革逻辑,也是劳役货币化的基本逻辑。
“免役钱”是国家财政统筹与货币化努力的直接结果,由“差”改“雇”(募),雇佣的本质在于货币结算,货币结算则要求个体劳役充分地货币化,熙宁役法在开始阶段,除了部分可替代劳役外,几乎没有给差役留下太大空间。那么这里“货币化”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观察。
首先,货币化的背后是某种均平诉求。免役法令民户均出“免役钱”,然后募人充役,随本役轻重给钱。其他如坊郭户、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等原无差役者,按照等第均出“助役钱”。这种“出钱免役”的方法整体改变了乡村差役格局和力役兑付方式。新法意图通过货币化来实现乡村力役的均衡摊敷,以应对旧差役制度下的不均性、机会性、人为性等问题。毕竟从理论上讲,货币可量化,兑付方式简明清晰,比人为品定差役要客观得多。但事实上,货币主导下的均平模式依然会被体制本身所限制,版籍、户等、财产制定标准、地区差异等是最大的牵制因素。劳役货币化对税收的均衡性提出了很高要求,“时免役出钱或未均,参知政事吕惠卿及其弟曲阳县尉和卿皆请行手实法”,于是相继产生了一系列辅助政策,但又引发基层强烈反弹。熙宁七年诏:“闻淮南路推行新法,多有背戾,役钱则下户太重。”熙宁九年,荆湖路察访蒲宗孟言:“两路元敷役钱太重,民间出办不易,至每年所收,广有宽剩。”元丰二年,提举司言:“乡村下等有家业不及五十千而犹输钱者,坊郭户二百千以下乃悉免输钱,轻重不均。”所以,免役法推行近十年,政府依旧还在为役钱不均问题所困扰。只是从“差役”到“免役”,人们对均平问题的考量方式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个体劳役的不平等性转变为货币均敷的不平等性。
其次,免役法使劳役的“量化”“统筹”和“预算机制”开始进入一般财政程序。就承役者而言,不同等级的差役可以通过货币来权衡轻重与风险大小,谓之“依轻重制禄”(可“量化”);就雇役端而言,被雇者的劳役以货币的形式完成结算(可“结算”);就国家层面而言,通过适当的预算机制来测算某地区的役钱总额、实际支出以及预留宽剩比例(可“预算”)。这样,承役端与雇役端通过政府的财政统筹来完成劳役交接,以及其它类型的财政支出。熙宁九年,诸路上司农寺岁收免役钱:收1041万贯硕匹两,支648万两贯硕匹。免役钱收支总额虽仍以“贯石匹两”计,然而细分到各地区,从开封府路到两广路,基本以钱“贯”或钱金银“贯两”计算,实物收支结算仅占据极少数。再看免役钱的规模,至“(元丰)七年,天下免役缗钱岁计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役钱较熙宁所入多三之一”。免役钱的规模一点也不亚于同时期的常平借贷,而在货币使用占比上(征收与支出)只会比后者更高。
我们可以看到,全国乃至各地的基层劳役被清晰地量化为一组组免役财政数据,并开始纳入国家的财政统筹中。免役钱除了作为主项雇佣经费支出外,还要进一步对接全国吏禄、水利基建、灾伤准备种种。在征收之前,这一切都是事先纳入政府预算的。王安石云:“不正用雇直为额,而展敷二分以备吏禄、水旱之用”“常留二分宽剩,以为水旱阁放之备”。而更重要的支付导向在于吏禄,“用免役钱禄内外胥吏”。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全国范围内胥吏“劳役”的货币化。根据王安石的《周礼》“稍食”观,即凡为公家付出劳动的,理当获得相应报酬(“稍食”),与其公然受贿为生,不如合法予之。王安石云:
三司所治,多是生事以取赂养吏人……人主理财,当以公私为一体,今惜厚禄不与吏人,而必令取赂,亦出于天下财物。既令资天下财物为用,不如以法与之,则于官私皆利。
又熙宁四年五月,
上又言:“曹司都不与禄,反责其受赇废事,甚无谓。”安石曰:“本收助役钱有剩者,将以禄此辈。”上曰:“以见役钱便可早定法制,使知。”
吏禄是一笔大宗经费,免役钱是其重要来源之一。“京师岁增吏禄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监司诸州六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缗。然皆取足于坊场、河渡、市例、免行、役剩、息钱等。”以京师开封的变化为例,“初,京师赋吏禄,岁仅四千缗。至八年,计缗钱三十八万有奇,京师吏旧有禄及外路吏禄又不在是焉”。从几无吏禄到全面赋禄,包括全国范围的胥吏阶层收入和部分基层县官的增收,每年度如此大的财政开支基本是通过新法的货币手段与财政统筹进行运作的。
第三,货币财政所实现的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宋人对货币的权衡与量化特征已有了初步认识,谓之“多寡有准”。货币财政的重要特征就是对货币机能充分利用。免役法为解放农村劳动力和游手安置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以货币预算、结算来实现力役的调配,漆侠先生评价“免役法的实施,用货币代替了极大部分差役,从而使劳役制残余更进一步地缩小,这不能不算是一个进步的表现。”
劳役的货币结算在历史上有过先例,但是以如此大规模货币化方式,甚至是“全面货币化”来驱动劳动力配置,在历史上是从来未有过的。汉代“践更”“过更”法似曾为货币化的一线曙光,但“践更”法仅限于私人雇募,“过更”法虽由国家统筹,但只针对“三日之戍”。唐租庸调之“庸”基本以绢帛等实物形式兑现,两税法货币、实物并行,“庸”已纳入其中而差役不免。以上种种终究没有免役法这样全面以货币为主导方式。
当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吕惠卿提出“给田募役”模式,以实物性的土地作为劳役报酬。说起来依旧还是免役、雇募模式,仅结算方式发生了变化。但哪怕是一点点的实物补偿倾向,也遭到王安石的激烈反对,成为他们师徒政见隔阂、日后分道扬镳的重要导火索之一。王安石重新上台后,首要的便是罢去给田募役法,恢复原免役钱征收模式。
第四,货币运作机制一旦成型之后,就会迅速拓展并进入模式化发展进程。青苗借贷模式与免役模式完全可以理解为两套不同的货币运作机制。
首先,青苗法代表着货币借贷及利息机制,“常平之息,岁取二分,则五年有一倍之数;免役剩钱,岁取一分,则十年有一年之备”。不仅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可以用来借贷生息,原则上所有的“闲钱”都可以如此操作。这是王安石变法以来的一个重要现象,以至于“常平青苗例”成为了财政运作上的一项“惯例”。其次,免役法则代表货币预算和货币结算机制,意味着劳役服务与部分上供义务都可以货币方式来结算。因此在免役法之后,顺理成章地就会出现“免行法”。
初,京师供百物有行,虽与外州军等,而官司上下须索,无虑十倍以上,凡诸行陪纳猥多,而赍操输送之费复不在是。下逮稗贩、贫民,亦多以故失职。肉行徐中正等以为言,因乞出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故有是诏。
免役法与免行法其实是同一原理,前者针对基层劳役,后者面向京师诸行上供。不管是乡户劳役还是行户上供,新法之后都纳入货币结算,以“役钱”的形式承担。因此,“免行钱”一开始就被称为“免行役钱”。这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免役法在京师行户领域的延伸。它的征收模式、转移支出形式也与免役钱高度雷同:也是按照财产标准,也是面向吏禄。详定行户利害条贯所奏:“应开封府委官监分财产,当官议定,或令探分,毋得辄差行人。……今众行愿出免行钱,乞从本所酌中裁定,均为逐处吏禄。”
结语
宋代财政与经济的货币化进程中,王安石变法时期是关键性的尝试与突破时段。新法开启了新的经济与财政模式,并以大规模货币运作为导向。常平新法执行青苗钱借贷。在还贷时,政府虽然设置货币与实物双选可能性,但通过极为低廉的“粮食基准价”设定,驱动农民选择货币还贷。青苗借贷的现实指向性与操作性,实质上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货币借贷闭环。与此同时,也引发了新旧两派关于实物与货币借贷的论战。免役法则进一步拓展了货币化的广度与纵深,开始由农业生产领域深入到基层劳役领域:分别从劳役执行模式、结算法、财政统筹三方面展现出深层的变革逻辑,也是劳役货币化的基本逻辑。
王安石变法中的货币化问题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课题,除了本文所探讨的青苗、免役二法之外,尚有均输、市易、盐茶(钞法)、货币铸造等诸多面向。尤其是市易一法,其商业借贷模式、货币机制以及由此产生诸多经济功能,又是自成系统。至于整个新法体系背后更深刻的经济与货币运作逻辑,笔者将另文专论。
原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删减注释后推送,引用务请参见原文。
作者简介
俞菁慧,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文字编辑:杨鹏颖
获得更多讲座、学术信息
电子邮箱:history@cnu.edu.cn
推文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告知我方进行删除
温馨提示:注:内容来源均采集于互联网,不要轻信任何,后果自负,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若本站收录的信息无意侵犯了贵司版权,请给我们来信(j7hr0a@163.com),我们会及时处理和回复。
原文地址"俞菁慧:王安石变法中国家经济与财政行为的货币化导向——基于青苗、免役二法的考察丨202212-92(总第2215期)":http://www.guoyinggangguan.com/xedk/210458.html。

微信扫描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